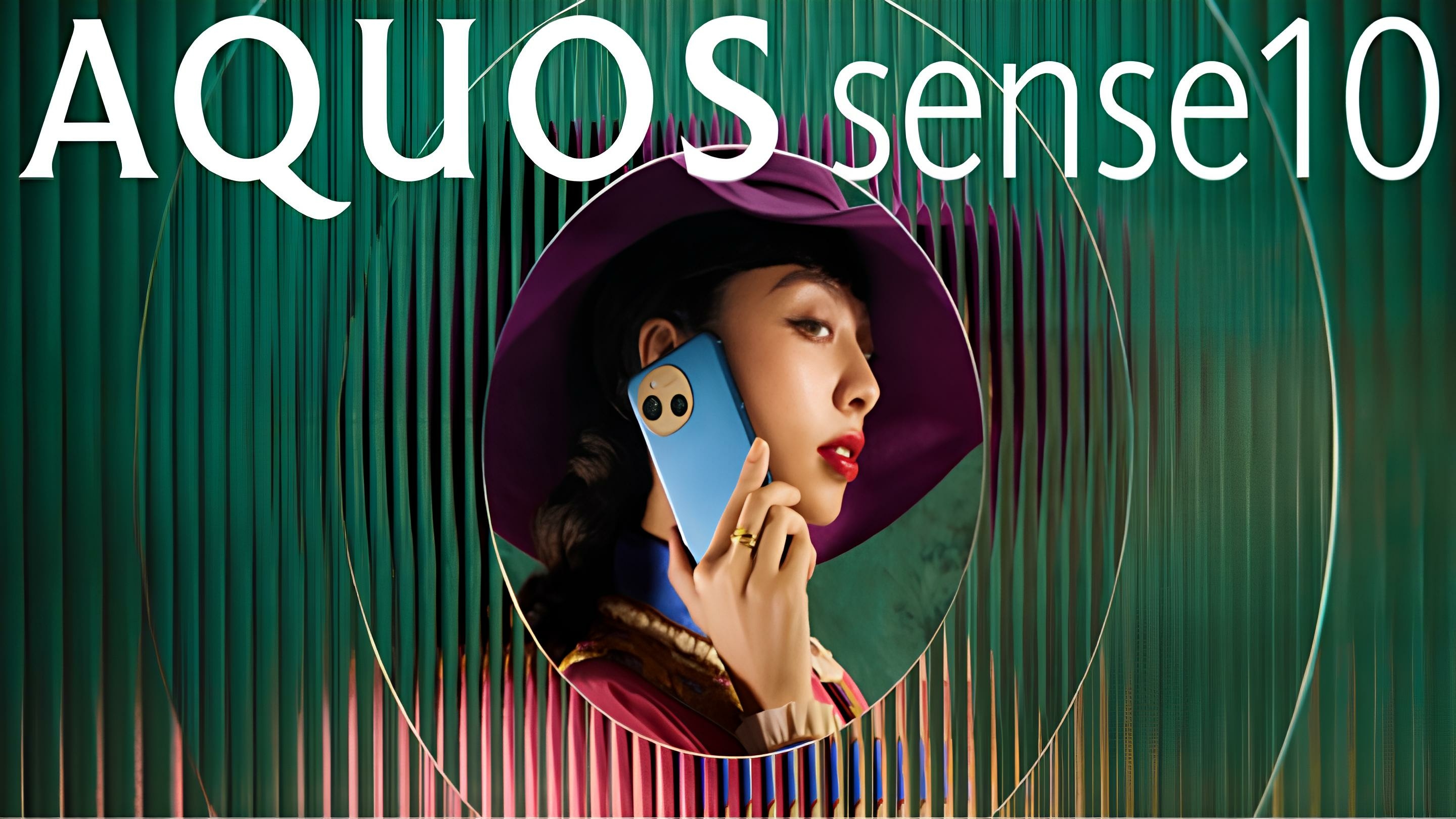自聯絡上老同學典婉之後,
得空便到她的中時部落格去瞧瞧。
今天發現了一篇新文章,是關於油椎ㄟ的回憶。
從小逢年過節就看著母親忙裡忙外的為年菜糕餅蒸、滷、炒、炸。
客家甜粄自是不用說了,
永遠是過年的首要第一個要蒸的年糕。
其次是菜頭粄﹝蘿蔔糕﹞和發粄﹝發糕,一般都是用瓷碗裝磨好的米水直接蒸熟﹞。
接著便是炸油椎ㄟ了
﹝其實是糯米+麵粉+地瓜和在一起搓成圓球沾上芝蔴下去炸成的芝蔴球﹞。
印象中,母親總是先秤了計算過的糯米拿去鄰居家磨成米水,
然後裝在痲粄袋綁緊封口,再用一塊大石頭壓住,
連同板袋綁在木頭萇板凳上,
下面則是放著鋁製的大腳盆去接滴下的水,
必須反覆的去翻動它,
或者是讓它經過一夜等米水乾了變成固體狀,
然後才可以和麵粉一起搓揉出彈性相當的似麵團一般的粄。
母親這時候會將蒸熟的地瓜磨成泥加入,再一次次的搓揉,
然後段成一粒粒大拇指節目大小的麵坨,
由我們這些小蘿蔔們把它搓成圓形之後沾上白芝蔴放在舖了一層蔴布的竹籠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不會掌控沾芝蔴的技術和力道,
不是沾太多就是沾太少,
母親也總是笑笑的看著我們嘻鬧,
溫柔的教導我們正確的方式,
甚至有時還得把我們搓成方型的芝蔴球重新搓過。
在原木的大圓餐桌上,
我們小孩幾乎都是跪在木椅上在玩著搓揉的遊戲。
在那歲末的寒冬裡,為了搓芝蔴球,
小孩們可是一個個的都把袖子給捲到手臂高呢!
而在那些芝蔴球都搓完成之後,
便是等待收圓的時刻了。
但是,因為需要高溫的油才可以炸芝蔴球,
對小朋友來說是危險的場所,
所以通常都是由母親和父親兩人動手,
我則負責帶著弟妹們回房間去玩。
我小時覺得媽媽是天下第一萬能的媽媽。
因為她好像什麼都會!什麼都難不倒她。
後來母親想出了新點子,
在芝蔴球裡面包一些黃糖和芝蔴再下去炸,
結果又成了另一種口感。
我想這是因為在那困頓年代中,
母親想出的可以讓我們孩提體驗零嘴的機會吧!
這幾年,世局改變太多。
弟妹們也都搬到中壢居住了。
頭份老家只剩父母親居住。
習慣了左鄰右舍如自家人般的生活,
適應了街坊鄰居噓寒問暖的親切,
父母親不願意搬家。
逢年過節時候,為了配合弟弟上班的休假日,
媳婦們也總在最後一刻才出現在公婆家。
而已經 76 高齡的母親也總是不放棄自己動手炸油椎ㄟ的習慣。
甚至還會一年比一年多炸一些,
然後分送給親朋好友,
當作供桌上對祖先們最溫暖的獻禮。
今天打開冰箱,看著那一袋油椎ㄟ,哎!
是我年少至今過年時節難忘的滋味呢!
媽媽,我愛妳!您辛苦了!

◎難忘媽媽的油椎ㄟ的滋味◎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